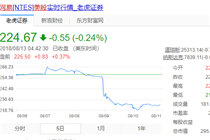这一系列包含“批评的向度”“历史的视线”“文化的逻辑”“媒介与现实性的扩张”等多组文章,邀请中、日、韩相关领域卓有精进的研究者、有志于游戏研究的青年学人以及游戏行业的前辈/从业人员等产学研各方面的游戏同好联合撰稿:尝试提出游戏批评的概念与观点,围绕游戏批评的价值、可能、向度、路径等展开讨论;以历史为向度,在文化与技术、东亚与全球、现代与后现代等脉络下呈现游戏史的源流及面向,梳理与探讨游戏文本与社会文化思潮之间的关联,表明游戏在从玩具向文化媒体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性特征;以批评的眼光,考察当下游戏世界的内部性原理。辨析当下中国游戏工业独特的支配性文化生产机制,并在此之外,探寻游戏(业)文化是否存在新的可能;聚焦于游戏对传统媒介的再生产以及现实因为游戏而发生的改变。此外,这一系列还包括关于游戏与性别话题的多篇文章,考察作为推动游戏“进化”的原动力——性/别,讨论游戏中的性/别议题;以及关于游戏的人的多篇文章,聚焦网管、主播、金币农夫、代练、电竞选手等年轻人,他们多是游戏这一领域里的边缘/异色人群;最后还会为读者推介一些海外书目,这些著作以游戏为媒介,讨论游戏背后的宏大构图,曾经并且正在为日韩的游戏批评提供着参照系。

日本动漫《记录的地平线》
前言
游戏无疑已经深入现代文化生活的所有角落,成为了当今最普遍的媒介之一。游戏机、电脑、手机,所有这些生活必备设备中都可以看到游戏的影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几乎所有人都成为了“玩家”。同时,游戏的无所不在已经使其成为了一种“环境”。
作为一种“环境”的游戏对于人们来说到底是何种存在,它对我们的想象力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它是否有着滋养各种思想的可能性。而为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从不同的角度,通过不同的方法去多方面的思考游戏。
对于游戏机制本身的分析,以及对其内部的作用形态的分析无疑是当今最主流也是很有效的方法之一。但是在探讨游戏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及文化意义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同时尝试其他的方法。
在游戏大国日本的亚文化产物,尤其是从1990年代开始人气不断上涨的动漫等“二次元文化”中,会频繁地出现游戏的“表象 representation”。所谓“表象”,不仅仅是在表面上采用游戏的形式或借用游戏的相关元素,而是将游戏和游戏中的各种设定作为想象和思考的框架来建构作品内容和世界观。换句话说,游戏成为了一种思考、想象以及理解世界的框架的同时,也是对游戏和现实的关系本身的反思。实际上,不仅仅是日本,就连欧美,甚至中国的各种文化产物中也出现了大量的游戏的表象,对于很多人来说,《头号玩家》的流行可能还记忆犹新。
这种作品的大量出现和巨大的人气,说明游戏所带来的想象力已经扩散到其他媒介(media-mix),同时也体现了游戏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媒介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看出对于人们来说游戏到底是什么,对游戏有着什么样的期待与寄托,作为一种想象力的框架,游戏如何反映并扩张着我们的现实认知,而其背后的文化环境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结构变化。
一、“现实与虚构”对立的解构——《记录的地平线》的“思想实验”
为了思考这些问题,笔者将以日本动漫《记录的地平线》这一颇具代表性的作品为中心,通过对作品中的游戏表象的分析,来弄清游戏所带来的新的想象力结构和由此生成的思想形态。简单地说,对于《记录的地平线》来说,游戏不仅仅是一种娱乐,而是一种规定玩家的人生观、自我观、社会观的“世界”,也因此有着作为另一种“现实”的强度,而以动漫的形式来描写和模拟这种“世界”,可以说是对游戏经验的一种深入的反思和挖掘,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反思性的“思想实验”。
《记录的地平线》(LOG HORIZON)是橙乃mamare所创作的科幻、奇幻小说,2010年在日本小说投稿网站“小説家になろう”上发表,后被日本著名游戏设计师桝田省治发现并由其主导出版书籍版,并在2013年被拍成动画。作品的舞台是老牌MMORPG游戏“幻境神话”成为了现实的世界。主人公城钟惠在某天突然发现自己以“冒险者”(在“幻境神话”中对玩家的称呼)的装束,出现在“幻境神话”游戏中玩家们的主城“秋叶原(アキバ)”,而与游戏时代通过显示器看到的世界不同,这里的一切感觉都是那么的真实。同时全世界有几十万人,仅日本便有三万人的玩家,和城钟惠同样被转移到了游戏世界,并且无法退出。这个世界其实是沿袭游戏设计的异世界,理解了这一点的主人公开始在这个世界中恢复秩序,建立公会,致力于原来被称为“大地人”的NPC们的人权和共存,同时摸索返回原来所在的世界的方法。
乍一看来,这部作品的设定是一种从现实世界跳转到虚构世界,并想办法回归现实的故事,这类故事也确实已经成为了一种“古典”类型,广泛出现在各种作品中。比如说《刀剑神域》这部作品便是一个典型,而因为两部作品在设定和世界观上的相似,所以经常被受众放在一起来讨论。但是重要的是,《记录的地平线》虽然采用了这种设定,并在故事的初期延续了“现实与虚构”这个古典对立形式,却随着故事的进展,这个对立本身却被不断地重新思考并解构,这也是笔者选择这部作品当做中心文本的理由。
主人公在故事的最初便宣称,“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现实”,并且在讨论现实世界和游戏世界的关系的时候,他从来都不会使用“现实”、“虚构”这样的话语,而是将现实世界称为“我们之前所在的世界”,将游戏世界称为“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或者“不同的世界”,也就是说在他的意识中,两个世界并不是“现实和虚构”这样的有着等阶序列的关系,而是两个在重要性和现实性上没有任何区分的“并列”且互相平等的关系。
在这个世界中,NPC不再是只是游戏设计者所设定的没有精神,只会按部就班的行动和说话的“人偶”,而是有着感情、思考、生活和文化的真实存在。因此在故事的初期,主人公最早遇到的反派人物迪米夸斯便是一个只将“大地人”视为“人偶”,并像奴隶一样支配着他们的冒险者,同时迪米夸斯也坚决否定游戏世界的“现实性”。
[这个反派冒险者对主人公说的一句话很具有代表性,即“这是我的世界,我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事情不顺我的意愿”。]
越是资深的玩家就越难以将NPC当做真实的人类来对待,也因此将NPC重新定义为人类便成为了故事中具有戏剧性之处,在这里有一个很明确的感情上的倾向性,即不管这个世界多么的和游戏系统相似,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原住民也是真实的人类。也就是说,在《记录的地平线》中“现实与虚构”这个对立本身是一个必须被否定的“敌人”。
游戏世界在这里获得了其作为“真实世界”的正当性,因此这部作品的主题就成为了对这个世界本身的独特性的阐释和演绎。首先,在“幻境神话”中,作为“冒险者”的玩家的存在意义被重新定义,他们没有必要辛辛苦苦的工作,每天从事打怪这种单纯劳动便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这种状态在主人公看来不能说是“活着”,只能说是一种“没有死”的状态。重要的是,在这个世界中冒险者并不会真正的死亡,而是如游戏一样死后会在神殿中重生。《记录的地平线》却通过这个设定重新定义了生与死的意义,在这里真正的死亡并不是消失,而是因为丧失目标和自我而萌生“想死”的状态,对于很多冒险者来说,和这种状态相比,真正的死亡是一种解脱,一种恩宠。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中,死亡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而是社会和伦理上的死亡,而这种死亡同时要求我们对“生”本身进行再定义。
[本作导演的石平信司在采访中说道:“‘来到这个世界后就没有办法死亡’ 所以 ‘那活着到底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反倒被重新提示出来。” (アキバ総研「NHKアニメ「ログ・ホライズン」監督&プロデューサーインタビュー!監督が最初にハマったのは、デミクァス(笑)」2014年03月13日)]
因此在这个世界中真正需要的是“除了只是活着以外,某种能够填满心灵的东西”。在作品中这种“填满心灵的东西”便是自己的“容身之处”,也就是所谓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可以是几个玩家所组成的公会,也可以是更大的组织。主人公也建立了自己的公会,并成立了一个统摄整个秋叶原的玩家和公会的自治国家“圆桌会议”,来维持秩序,建立经济体系,并为冒险者们提供各种可以参与的节日活动。
[石平信司导演在采访中说道,“在一种连死都不能的,永远被关在游戏中的糟糕情况下,建设共同体”是这部作品的中心,使其成为了一种“社会派戏剧”。(并且“正因为我们在拥有着无限生命的游戏中,如何面对他人,如何进行交流”才是这个作品的中心。アキバ総研「NHKアニメ「ログ・ホライズン」監督&プロデューサーインタビュー!監督が最初にハマったのは、デミクァス(笑)」2014年03月13日)]
“共同体”有着各种各样的定义,而在《记录的地平线》中,它的主要作用是为个人提供容身之处,在与公会的战友的交流中化解“我是谁?” “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孤独和迷茫,为人们提供生存的意义。在这个无法真正死亡的世界中,“守护”某个人的意思就是为他或者她创造一个可以安居的“共同体”。也就是说,“共同体”是一种在不安定、不透明的、过分流动化的社会中为个人提供“自我同一性”的基础的存在,而这同时也是MMORPG等类型的游戏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所发挥的功能。
正如动画第二期第十话中“银剑”公会会长威廉所倾诉的,他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不合群,就算活着,没有朋友也没有目的,但是在游戏中他可以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活着的意义和乐趣,这多亏了游戏中的朋友的存在,不管周围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们如何骂自己“死宅”,如何强调“游戏是在浪费时间”,它提供了现实所无法提供的东西,填满了自己的心灵,让自己关心他者,并知道了如何理解他者的内心和烦恼,学会了如何和别人产生联系。尽管自己仍然是一个无法融入社会的人,尽管游戏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但是它告诉了自己所有重要的东西,所以“特别厉害”。
[在一个与扮演威廉的声优的对谈中,导演如此描述了这个场面:“威廉代表着全日本的游戏玩家诉说着,听了这些都不会被感动的人,没有资格说自己是玩家!”(ファミ通.com,「テレビアニメ『ログ・ホライズン』第2期ついにスタート! 石平監督、寺島拓篤さん、中村悠一さん、藤井ゆきよさんインタビュー」,2014年10月10日)]
在这里,沉迷于游戏的“死宅”成为了一个能够理解、关心他者的,极具伦理性的人物。而且需要指出的是,《记录的地平线》在第一期第四话之后故事的中心就转移到了人物的对话上,也就是说这部作品不管是从演出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蕴含着一种明确且一贯的思想,即不管是“现实”还是“虚构”,认识他者并让自己对其开放的“交流”过程本身才是真正重要的。
[“正因为我们在拥有着无限生命的游戏中,如何面对他人,如何进行交流才是这部作品的中心问题。“(アキバ総研「NHKアニメ「ログ・ホライズン」監督&プロデューサーインタビュー!監督が最初にハマったのは、デミクァス(笑)」2014年03月13日)]
而常识中“现实”的权威性被相对化,“现实”和“虚构”成为了一种处于互相对等关系的“媒介环境”,它们都为这种交流过程提供手段。因此,这一逻辑上的必然归宿就是,无论我们选择哪种媒介都有一定的正当性,而真正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去如何选择。
由于在“幻境神话”中,玩家在死亡和重生之间的短暂时间里可以看到自己之前所在的世界的记忆,因此急切想回到原来的世界的“奥德赛派”,就会不停地让自己在战斗中死亡,就为了一睹短暂的“现实世界”的幻想。这里存在着一种等阶序列关系上的逆转,也就是原本拥有绝对权威性的“现实世界”在这里反而成为了一种从“这个世界”逃避的虚构。
在这样一种两个世界相互对立的情况下,到底是留在这个世界还是想办法回到原来的世界,就成为了包括主人公在内的所有冒险者都面临的急需抉择的问题。如作品中的人物所说,“这个世界虽然不是他们自己选择来到的地方,但是在所谓的“现实世界”中出生同样不是人们自己可以选择的”,并且两个世界作为一种为自己提供生存意义和交流场所的“媒介”都同样的真实、具体,所以主人公如何选择成为了作品最后的高潮,而演出这种两难局面的意图便在于最大限度引起现代社会中游戏玩家们的共鸣。
因此,如何去解决这一两难,便成为了最能直接体现这部作品“思想”的部分。也就是说,在相对化了“现实”的权威性和独一无二性,并到达一种什么都不是可以绝对相信,也因此什么都可以相信的地点之后,我们的选择所体现的就是我们和两个世界的关系,以及我们对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的态度。
《记录的地平线》避免了“回归现实”这样一个“政治正确”的态度,也没有决定沉浸在异世界中,主人公的最终的答案是让两个世界并存,同时让两个世界的人们可以自由来往。这意味着对两个世界双方的肯定,也意味着对这种“双重现实性”共存的世界本身的思考。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将其放到更大的脉络中去思考,并由此更为深入地挖掘出其背景和可能性。
二、“双环境化”的日本
“现实”权威的瓦解,“现实”和“虚构”的并存和对等性,以及辩证性的将二者全部囊括进来的一种全新的世界认知所产生的新的主体性和伦理性,这便是我们在上一节中通过对《记录的地平线》的分析看到的一种想象力和“思想实验”,而孕育了这种特殊的世界想象的正是日本的文化环境。
如大塚英志和东浩纪等论者所说,战后日本的文化环境在其发展过程中,将虚构作品作为中心媒介最终形成了一种巨大的人工环境,而这种人工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一种新型的“现实性”的诞生。这种新的“现实性”的形成在文学领域体现的最为明确,比如说在日本年轻人当中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轻小说”,它有着和近代以后的文学完全不同的发展过程。日本的轻小说很难定义,科幻、奇幻、青春、侦探等类型都可以包含其中,虽然主要读者对象是初中生和高中生,但是轻小说的内容并不“轻”,它们唯一的共同点便是都有着以动漫式角色为中心的封面和插图,而其实这正是区分轻小说和纯文学或者现实主义文学之处。据大塚英志所说,现实主义文学所描写(写生)的是我们的现实,但是轻小说所描写的却是漫画和动画,并将其命名为“动漫现实主义”。
[大塚英志:『キャラクター小説の作り方』講談社,2013年。東浩紀:『ゲーム的リアリズムの誕生:動物化するポストモダン2』講談社,2007年。]
也就是说,由于动漫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存在,形成了一种新的现实性,使“虚构的写生”这样的文化习惯得以实现并普及开来。
日本的社会学家稻叶振一郎更是将现实主义文学和动漫、轻小说、游戏等幻想类的虚构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此为基础来讨论“公共性”的问题。在稻叶看来,近代文学在诞生之时所采用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因为它以“描写现实”为理念,而是因为近代文学抵抗近代之前的文学中的“约定俗成”并寻找它的替代物之时, “现实”作为一种能够被所有人所共有的文化素材和经验(common knowledge)而被采用,因此可以说现实主义的采用和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交流效率”的最大化为背景的,而现实主义也成为了近代以来的公共性的基础。与此相同,动漫、游戏等二次元文化在日本的普遍化使其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被大多年轻人所共有的文化经验,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作为媒介的二次元文化也成为了一种可以使“交流效率”最大化的“约定俗成”,而这和现实主义一样,同样可以成为一种“公共性”的基础和媒介。
[稲葉振一郎:『モダンのクールダウン(片隅の啓蒙)』NTT出版,2006年。]
ACG等二次元文化作为一种在后现代的日本已经充分普遍化了的媒介环境,已经成为我们生存和思考,以及文化想象力的基础条件。
重要的是,在这个视角中,游戏的重要性是比动漫等媒介更加突出的,比如说我们在看奇幻或者“软”科幻等虚构作品的时候,其实作品和我们的现实是互相独立存在并且没有交集的,但是游戏媒介的即时反馈却可以让我们在虚构的世界里活动,交流,建构共同体,甚至结婚。也就是说,游戏可以让我们在真正的意义上“生活”在虚构的世界当中。对于年轻人来说,游戏是最“真实”的奇幻世界,或者反过来说,游戏使奇幻和幻想更加“真实”。玩家们对游戏式的设定、规则、互动方式的熟悉,形成了一种想象力的框架,而虚构世界也因此获得了很强的“现实性”。
不过这并不代表当代的文化环境已经从现实主义转变为“虚构主义”,而是两个环境同时存在于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也就是说,除了现实主义之外,ACG也成为了一种“想象力的环境”,东浩纪将后现代的这种情况称之为“想象力的双环境化”。在上一节中的对《记录的地平线》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作品在最初就两个世界的共存和对等性作为了故事内容的中心,而这种想象力正对应着日本社会整体的“想象力的双环境化”,或者更准确的说,《记录的地平线》的想象力和感性,以及思想倾向本身就是以日本的这种文化环境为背景而出现的。
但是最重要的并不是两个世界(环境)的共存,而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现实与虚构的两个世界并不是相互独立且毫无交集的。在《记录的地平线》的最后,主人公选择了让人们在两个世界间自由来往和交流,这意味着两个环境的融合本身便会形成一个更大的、新的环境结构。而当下日本社会乃至世界所身处其中的,正是这种两个想象力互相融合、互相影响的新的环境结构,《记录的地平线》所依据的想象力和“现实性”也是从此处所产生的。例如东浩纪在《游戏现实主义的诞生》所举的例子,以《凉宫春日的忧郁》系列以及新海诚的作品等为代表的“世界系(セカイ系)”的作品的典型模式便是,在普通的高中过着普通的日常生活的同时,自己或者同学在为了保卫人类和地球而战。
[東浩紀(2007),96-97页。]
这两种“现实”的直接连接,正体现着两种想象力的环境的共存,不仅在日本,这类作品在中国和亚洲的巨大人气,以及在其影响下诞生的大量的同类作品证明了这种新的环境结构的存在。
三、“虚构内存在”的伦理性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为什么需要讨论这种新的环境结构?它在哪些地方值得我们重视?
如诸多论者所反复强调的,我们身处于一个危机的时代,一个所有事物都变得复杂至极,不断地变化,不断地流动,完全超过我们的把握,使我们陷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由其引起的深深的恐惧的时代,鲍曼将这种时代的恐惧称之为“流动的恐惧”。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恐惧》,徐朝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而我们每天所感受的,所见闻的各种现实的事件,和他人的交流,无不是通过媒介来进行的,而且在大众媒介和社交媒介发挥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人们日常中只能通过这些媒介来与大量的他者共存的境况下,从中产生的“现实世界”的观念本身就是一种想象性的事物。在这样的时代中,“现实”本身其实就处于一种极为不安定的流动状态,因此,以《记录的地平线》为代表的各种日本二次元文化中出现的“现实的相对化”本身并不是游戏玩家的一厢情愿,或者动漫爱好者的自我辩护,而是一种确凿的现实和必然的归宿。用日本批评家藤田直哉的概念来说便是,在这个时代,我们都是生活于现实和虚构二者共同塑造的环境中的“虚构内存在”。
[藤田直哉:『虚構内存在――筒井康隆と〈新しい《生》の次元〉』,作品社,2013年。]
也正因为如此,如果在这个时代还继续坚持“纯朴”的“现实主义”式世界观,其弊端也将清楚地暴露出来。如稻叶所说,原本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功能和理念是以所有人类所共有的“现实”和由其所形成的“常识”作为交流的素材和媒介,将其向尽量多的人群乃至全人类开放,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所期待的是对他者和他者的世界的理解和接受这样一种伦理态度和公共性的形成。但是,不管是“后现代”还是“后殖民”,各种文学、文化研究都告诉我们,这种普遍性其实也只不过是在极为“地方 local”的共同体中通行的“约定俗成”的一种,并且在“双环境化”的境况下这一点也越来越明确。更加严重的问题是,由于“现实主义”有着“自己所描写的是唯一的现实,因此这种普遍性和公共性是毋庸置疑的”这样的自负和幻想,而将其他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共同性排除在外,甚至进行暴力性的迫害。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想起在第一节对《记录的地平线》的分析中提到的,“银剑”公会的会长威廉的作为一个玩家对来自于“现实世界”的迫害的抗议。在拥有着“普遍性”的现实世界看来,游戏的玩家只是在逃避现实,他们的游戏内行为完全是毫无意义的,这种行为不仅伤害着他们自身的生活也对社会整体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因此需要排除和矫正。这种对“他者”的迫害在日本作为一种社会整体的压力和歧视存在,而在中国却不仅如此,如以杨永信为代表的“矫正”迫害,更是以实际的暴力形式进行着。
在这种情况下,“逃避现实”这个词已经成为了一种万能话语,从逻辑上讲,它可以用在对主流社会和经济政治逻辑造成了潜在威胁的、我们的所有文化生活上,也正因为如此,“现实”这个词反而失去了任何实质性的意义而变成一种虚构,它只是通过各种否定性的言辞勾勒出一个轮廓,而轮廓的内部却是空白的,可以往里面塞进任何主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最明显体现这一点的便是现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现实”和“弱肉强食”的话语。
[王晓明将现代的这种“普遍的消极意识”和“政治无意识进行了概括:“现实非常稳固和强大,我们不可能去改变它,只能去适应它。”“因为丧失了改变世界的信心,看人看世就容易消极,正因为难以体会理想的魅力,就更觉得只有物质利益才真实。”(王晓明《在“小器化”的时代里:今日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新世纪:反思跨境的东亚文化”国际研讨会,日本・东京,2017年3月18-19日) 也就是说,物质消费替代了“理想”,或者说“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记录的地平线》中所表现的对“虚构世界”的现实性的追求可以说是“物质消费”的最极端的对立面,而也因此有着作为思想的可能性。]
以上论述的目的并不在于正当化游戏玩家对游戏的沉迷,而是想通过对游戏这种建构真实虚构世界的媒介的分析,来弄清当今的“现实”和文化的结构,而不是在“现实主义”的幻想中对他者进行迫害。在本文的多处,笔者都将游戏媒介称为一种“环境”,它所意味着的是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注定被其所包围,在其中生活和行动并构建自己的生活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动漫现实主义”还是“游戏现实主义”,二者都是将文学的表现形式贴近文化现实本身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第二次“言文一致”的运动。]
而如果不接受这一点并对身处其中的人们进行单纯粗暴的批判的话,对于当事者来说是一种“双重的异化”,也就是说即否认了他们的生活意义的正当性,也否定了他们建构某种生活意义的基础条件本身,而后者是他们自身完全无法左右的。因此这种“双重异化”式的批判对于当事者的年轻人们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成为一种来自于持有特殊思想的人群的对“他者”的排斥,而不是真正的批判。这种排斥性的批判非但不会产生任何建设性的反思,甚至会磨灭掉在这种环境中可能诞生的批判性思考的萌芽。
《记录的地平线》的最后所提出的两个世界的共存和交流虽然只是一种理念,但是这种理念是建立在两个环境共存的现实的准确认知上的,也正因为如此,如何接受“他者”并向其开放成为了作品的核心主题。之前人们仅仅认为游戏中的“NPC”只是在进行单纯的机械式的行动(正如“现实主义者”眼中的游戏玩家一样),但是通过主人公对这个世界的正确认知和尝试交流的努力,最终使得其他人也渐渐接受了他们是真实的人这个事实(比如说作品最初将NPC的“大地人”当做奴隶一样鞭打使役的迪米夸斯在作品的最后选择了和“大地人”结婚)。同时,这部作品除了接受和自己不同世界的共存和交流之外,也提出了以积极的姿态去思考和处理由两个世界的共存所引发的各种各样潜在问题的重要性。而在“双环境化的想象力环境”这样的现实认知中,只有这种姿态才是在当代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下能成为一种真正的“伦理性”的,向他者开放的想象力的基础。
结语
游戏所建构的虚构成为了一个“世界”,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不可理喻且不切实际的主张,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游戏本身并不仅仅是一个作品或者一个商品,而是像当今其他新媒体一样,是一种“平台”——玩家在游戏中的互动和交流可以产生无数不同的故事。如果像本雅明所说的那样,摄影等媒介使文化产物的“大量复制”成为可能的话,那么以游戏为代表的新媒体环境的出现和普及就使故事的“大量生成”成为了可能。
[东浩纪将大塚的讨论进行了理论性的推进,称“轻小说的本质既不在作品的内部(内容),也不在作品的外部(流通),而是在作品和作品之间展开的想象力的环境(角色的数据库)之中。”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文化领域,需要的不仅仅是传统的作品的文本分析,也不是单纯的对作品外部的流通(政治经济基础)的分析,而是作品群和读者之间所共有的一种“想象力的环境”的分析。正如游戏一样,可以通过“replay”来生成无数个故事,而我们所共有的正是这种游戏性的环境,因此这种被称为“元故事性 meta-story”的环境在其本质上是“游戏性”的。東浩紀(2007),45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媒介转换的时代中,在这里我们的主体性、思考和批判的文化基底本身也迎来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无视这个现实。而如果这种本质是在游戏等新媒体之中所形成的话,“双环境化”的问题就不仅仅是日本,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了。
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游戏已经成为巨大资本的主要动力源,这种游戏将玩家的身心把握为某种具有“可塑性”的工具性对象,通过各种数据控制和调整来刺激玩家的动物性欲望,使其成为一种新型且极为效率的榨取方式这一事实。也就是说,现实的游戏产业与其说是一种思想装置,更像是剥夺反思能力的机械,所有人都变成了他们所设定的世界中的 NPC,而真正的玩家则是游戏的运营者。当然,也有各种功能性游戏,比如以教育、心理治疗、提高工作效率、增加人生幸福感为目的的游戏出现,“游戏化”一时间成为了游戏业界的新大陆。但是,这些功能性游戏同样以玩家身心的“可塑性”为前提,对其任意操控,并要求玩家对自己的身心同样持有“工具性”的态度,要求我们去适应现有的、支配性的规则,而不是改变它。在这一点上,它与前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
与其相反,游戏表象作为一种思想实验,所意味的是它是把握和理解世界的一种框架的同时,也是对现有的(游戏)规则和意识形态的怀疑和相对化,以及对另一种现实的可能性的思考。这种志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称为“逃避”,但是在“现实”话语成为至上命题之前,它曾经被称为“批判(批评)”。因此或许可以说,在现实话语的压迫下产生的“逃避”和“批判”的混浊导致了所有文化形态都在不同程度上变成了从现实的暂时“逃避”,并被赋予了一个边界暧昧的称呼:“文艺”。但是双环境化的世界要求人们对现实话语的支配性产生怀疑,重新要求思考另一种可能性的权利。同时,这种思想实验并非强调虚构和现实的对立,相反,它强调为了实现更好的社会和伦理,二者是不可分的。
[关于虚构(fiction)在普遍意义上的重要性,请参照以下文献。Schaeffer, Jean-marie. Why Fiction? .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Lincoln, 2010]
也就是说,虚构和现实作为一种双重化的环境被并列的结果,便是一种包含了这两种环境,并能对其二者的规则以及关系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元话语”以及与其相对应的感性的诞生,通过这种“元话语”,人们可以看到,现实已经不是那一成不变的现实,而虚构也已经不是让自己麻痹的娱乐。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有必要在接受《头号玩家》中的台词——“毕竟,我们还是只能在现实中吃一顿真正的饭”——的同时将其反转,即“毕竟,我们还是只能在游戏中感觉到我们不只是为了吃一顿饭而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