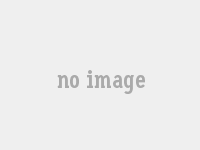近期一款名为《旅かえる》的游戏在ISO的排行榜上位居榜首,KAERU的发音有着双重的含义,一是青蛙(カエル),二是归来(かえる),顾名思义,这是关于一只在出外旅行和游后归家的青蛙的游戏。游戏的玩法也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主要就是在院子里收割四叶草,然后用四叶草去给青蛙买便当和道具,然后等蛙出门,等蛙回家,等收到蛙的明信片……很多人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都有一种当上老妈子的感受——孩子在外的时候盼他回来,孩子在家时希望他多出去看看这个世界,多交些朋友,无论是期盼儿子外出还是期盼儿子归来,“老妈子”们也是在“甜蜜的焦虑”之中度过的。
游戏的原型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游戏会有那么大的魔力呢?也许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是人类最先的游戏原型之一。弗洛伊德观察到他的小侄儿在玩一个扔线圈的游戏,把线圈扔出去,说“fort”,把线圈收回来时,说“da”,弗洛伊德把这个游戏解释为孩子正在模拟母亲的在场和缺席,通过模拟游戏的方式让与母亲短暂离开的痛苦变得可以承受。这种分离的焦虑不只是属于孩子的,母亲在孩子不在自己身边时,也会有这样的不安。但是游戏让这种焦急不安变成了一种乐趣,因为在游戏中我们处于规则的保护中,孩子不会把线圈真正地弄丢,正如旅行青蛙的规则里蛙儿不会真的离家出走,无论它去多远都有回来的一天。现代人只有在这种保障下才能去享受分离的乐趣。这当然不局限于母亲和女性,而是所有处于“养育者”的位置上的人来说。即使是养蛙游戏的男玩家,也是处于一个“蛙妈”的位置上,本文的“母亲”、“女性”指的与其是生物性别,不如说都是社会分工。
精神分析指出母亲和孩子之间存在着一种黏着的关系,一方面,孩子不想从绝对能满足自己的客体——也就是母亲分离,无论是谁只要出生在这个世界上首先要面对的创伤就是从娘胎(一个能满足所有需要的地方)到外部,所以上面说到孩子才需要用游戏来帮助适应母亲离开的痛苦;而另外一方面,母亲也不想小孩离开自己,希望小孩依然自己的东西,受自己控制。对于母亲而言怎么保持和儿女的距离和克服他们离开自己的焦虑是人母的重要课题。尤其对于“全职妈妈”而言,孩子就是自己的毕生事业,是牺牲了自己的家庭以外的社会关系后唯一剩下的东西,所以特别希望“占据”着孩子,对他有朝一日离自己而去、不受自己控制而感到焦虑。
因为母亲的这个欲望引发的问题不计其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八零九零后的年轻人找到了可以言说自己创伤的渠道,豆瓣“父母皆祸害”的小组聚集着各种对原生家庭的控诉。心理学家成为了两代人关系的法官,有的完全站在年轻人的一边认为他们有权利去表达对上一辈的愤怒,而有的人则充当“和事佬”的角色认为双方终究要和解。但或许对于两代人的“和谐”关系作出贡献的不只是心理学家,还有是经济政治层面上的女性主义运动,当越来越多的母亲出外工作,母子之间的黏着性就自然减弱了,这时候心理学的知识自然也很容易派上用场,母子成功地保持了一定距离。
但显然这并不会根除所有“来自母亲的创伤”,欧美的女性主义运动兴起得比中国早得多,出现了一批经济独立的母亲,但由此诞生了一批“缺乏母爱”的孩子。比如说著名导演拉斯·冯·提尔的母亲是一名左翼知识分子,经常参加社会运动,但对于家庭并没有留太多的心思。对母亲的矛盾情感充分反映在他的电影里面,一方面他入木三分地刻画了现代女性“不向欲望屈服”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毫不留情地表达了这种解放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在他的电影里至少两次出现了在母亲去享受性的快乐时忽略了孩子导致他从窗户里坠落(或差点坠落)的情节。保守派的欧美人会把这种现象阐释成一种“回归母性”的诉求,谴责现代的女性从母亲的所谓“天职”中撤离导致后代在“没有母爱”的环境中成长。
中国的母亲不得不同时应对以上两种压力,一是来自传统文化中对母亲角色的要求,即必须履行母亲的义务去培养孩子,而是现代化对女人的要求,必须运用你的自由去在孩子和其他事情之中作出选择,而且底线是不能对孩子太过控制。而心理学家在其中往往会创造一种“平衡”、“和谐”的神话,仿佛一个成功的女性可以兼顾两者,只要她具有某种“智慧”。但这种话语服务的不是母亲本人,而是“现代母亲”的社会形象,以及家庭-社会的利益,它要求女性去适应这个在转型中的母亲位置。
出于这种对女性的期待(再次强调当然这有时包括对“奶爸”的期待,本文的性别指的与其是生物性别,不如说都是社会分工),不难看出为什么现代人那么向往和蛙的关系:只需要闲时看两眼手机,就可以体验“养娃”的体验。同时也向往这个讲规矩的孩子,从不向自己提出什么让自己难为的要求。这仿佛是理想中的儿女,不同于现实中百般刁难、需要经历大量痛苦才能养育的孩子。既不打扰自己的正常学习、工作、休闲,也能体会作为养育者看着儿女时而出现、时而小时的甜蜜的焦虑。在精神分析的角度看来,父亲是让母子与孩子分离的角色,其功能是限制母子之间的过度亲密,而在模拟养蛙的游戏里,这个父亲的功能就由游戏的机制所替代,游戏里的孩子会乖乖地遵守程序编定好的规则,不会给“现代妈妈“们带来困扰。
那么现在很容易就会得出一种结论:既然养蛙游戏是一种被削减的现实,一种满足现代消费者需求的情感商品,那么我们该放下游戏去面对现实的复杂性了。而这样把游戏和现实对立的结论显然是荒谬的,现实也是各种社会机制造成的一个更为复杂的“游戏”而已。游戏告诉我们的不该是现实作为游戏的反面是真的,相反,是现实作为游戏的类比也是“假的”,也就是像游戏一样具有各种变动的可能的。
对现实的模仿
游戏确实能为我们提供了家庭的另一种想象,比如说日本的文字冒险游戏《家族计划》就讲了“天涯孤独的主人公、被公司裁员中年、中国的偷渡者、离家出走女孩、自杀未遂的女性等、被社会冷落的弱者们创建了一个拟似的家庭”的故事,把家庭这一个基于血缘关系维持的概念变成了“同一屋檐”下的空间性的概念。在历史中也有过这样的运动,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后让青少年脱离家庭在合作社里面自行组织生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虚拟的游戏和政治实践之间有种完全可以类比的“实验性”,可以激进地探索家庭关系的各种可能性,实验中遇到的新难题也往往会伴随着诗性的火花。
游戏为什么能够带来这种实验呢?关键是它是“模拟”的,游戏中的家庭关系和社会伦理中的家庭关系保留了一定的距离。当女孩子玩芭比娃娃的时候,当然可以说这是在接受社会对女性(尤其是母性)气质的灌输,但在这玩的过程中,她认识到母亲和母亲的身份是有一个距离的,正如自己在玩玩具时是在演妈妈,妈妈在陪我玩的时候也是在演妈妈,正如她可以停掉这个游戏,妈妈也可以停掉,这时当然会有焦虑诞生,但此时“我可以不是我的角色”这个种子已经埋下了。现在的电子游戏也是一样,一方面是对某种愿望的满足,另一方面也提醒着关系的虚拟性与潜在的可能。
所以或许最激进的“虚拟”并不是在虚拟中寻找现实的另一种可能,而是在虚拟中表演在现实中普普通通的事,让理所当然的坚固现实浮现出它虚构的本性出来。比如在电影《纪子的餐桌》里有一个“家人出租公司”,人们可以出租公司的职员来扮演自己家庭里的某个角色和自己相处一段时间。虽然我们在这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最普通最无聊不过的家庭,但是会有一种巨大的戏剧性效果,甚至会怀疑我的家人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在扮演家人的角色呢?我是不是也在扮演家人的角色呢?
哲学家巴特勒把这种虚拟称作“操演性”(performativity),简单地说,她认为女性气质并非生理性别决定的也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建构,而是通过女性对女性的“扮演”而达成的,就是说在每个人和自己的性别身份是有一定距离的。换到家庭上或许是一样的,母亲、儿女很大程度上都是像《纪子的餐桌》里一样表演自己的家庭里面的角色。与强化对某个身份角色的认同和接近的某些心理学话语相反,或许游戏给了我们与这些身份保留着反思性空间的可能性。
但是这个反思性的空间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察觉到的,因为在大多数的游戏中我们认同了某个游戏里要求我们扮演的角色(比如说“蛙妈”)。玩芭比娃娃的小孩子还可能会因为游戏的虚拟性而感到一丝不安(因为他们对世界经验的不足),而成人的世界是秩序井然的,在游戏中的扮演和对现实中角色的扮演已经是别无二致,也非常快地被接受了。我们能理所当然地灵活带上社会面具去“操演”各种角色,但是适应太快的代价就是会忽略这件事本身的不可思议。所以光是扮演还是不够的,我们或许需要“对扮演的扮演”而刺激我们的神经,比如影视作品里面有“戏中戏”(当然在现在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又比如“Meta游戏”,即对游戏的游戏,如在《史丹利的寓言》里面,玩家扮演的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跟随者旁白去感受自己和自己公司职员身份的不协调。Meta游戏尝试打破“第四面墙”,穿过玩家对他所扮演的角色的认同,直接和玩家对家,询问古老的哲学问题“你是谁?”但是可惜的是这类游戏的冲击难免还是像影视作品的戏中戏那样被适应,而一旦被适应批判价值就大大减弱了。
而今天由商业逻辑主宰的游戏业偏偏又是以讨好顾客为中心的,无论是以“新教伦理”为主导的爆肝氪金的手游,还是治愈的佛系手游,都是利用玩家的“适应”,不单只是适应一种重复的日常劳作,还是适应一种既定面具之下的生活:适应家庭、工作、社会身份……游戏渐渐变成了我们吃饱后能继续我们旧生活的小点心,而不是让我们吃了惊讶得把旧生活连拉带泻出来的毒药,但游戏是确实具有后者的潜能的。
随便看看
-
人民网总编辑罗华:发挥内容科技优势 深化游戏责任内涵
2020-10-14 20:07:26 -
“网络宵禁” 不会一劳永逸 还有更多要做
2017-01-18 11:11:33 -
你曾经熬夜奋斗的端游手游页游都被改成这个德行了
2017-10-13 18:00:31 -
明年单机游戏市场或有望持续走热
2017-12-29 19:01:22 -
Amy Hennig讨论游戏业未来/门槛/难度/受众问题
2019-04-15 23:30:07 -
广深游戏公司买量排行榜 做的好并非没有原因
2018-03-30 15:18:00 -
游戏行业该降降火了
2021-08-09 11:05:42 -
游戏还能怎样进化?
2021-08-09 11:03:35 -
“鱼虎”相斗流血上市,游戏直播该向何方?
2019-09-05 20:57:43 -
最强倒爷模拟器?《雷索纳斯》跑商玩法详解!
2024-03-07 17:06:45